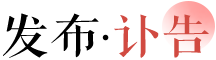一切都会好起来的
我用我给你贫穷的街道、绝望的日落、破败郊区的月亮,
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看孤月的人的悲哀,
什么才能留住你?
一朵黄玫瑰的记忆”
——《我用什么才能拥有你》博尔赫
最亲爱的姨夫:
你好吗?
这封信我自那天起就有了书写的念头,但却迟迟未曾下笔。因为不敢写,也因为不知从何写起,于是就这样自欺欺人地认为:只要不提及,一切悲伤就会不复存在,可是啊,那悲伤就像是没有完全愈合的伤疤,即使结了痂,内心的血肉仍是疼痛难忍的,连快乐都是沉甸甸的隐痛。
于是,我觉得是时候写下来了,也是时候,告别了。
我从书中看见过这样一段话,它说,一个人失去一位所爱之人就等同于失去一根肋骨,那块缺了骨头的地方就会成为你余生的软肋,我没想到,我的第一根肋骨竟然失去的如此突然,如此猝不及防。
2020年5月22日,是我放月假归家的日子,那天的黄昏弥漫着温热的潮气,粉红的晚风令人没由来的感伤。进了家门,只有父亲站在玄关处迎接我,母亲正在房间里痛哭,眼泪流淌成汩汩小溪,洗刷着母亲苍白的面容,我一再追问发生了什么事情,而母亲只是流泪,等我满腹疑虑地吃完晚饭,父亲才把我叫进房间,满面沉重之色:“珺儿,你姨夫,去了。”父亲说得隐晦,而我却瞬间领悟了,但仍是再三确认:“.......是姐姐的爸爸吗?”“嗯”“去了?什么意思?“......”父亲用沉默已然回答了我的发问,也证实了我心里的可怕的猜测:你离开了我们,永远不会回来了。
大脑昏昏沉沉,父亲以他极罕见的温柔帮我拭去汹涌的泪水,而我却只看见破败天空残余的一抹晚霞,觉得那颜色真是凄艳的令人心碎。
姨夫,你就这样毫无征兆地走了,永远地离开了人世,永远地留在了南疆,那片你不得不去的土地。
在泪眼朦胧间,我脑海中闪现的的画面:驻村两年有余,归期将至,此次你匆匆赶赴南疆就是为了处理最后的交接工作,谁也不曾想到,这次分离竟是永别。
你总是温柔而宠爱着我那不善言谈的姐姐,姐姐挑食且有诸多忌口,但你总是想办法满足姐姐的口味,姐姐一向内敛,所以你总是担心她在外受了委屈,对于姐姐这么多年的教育费用,你从未有过一句怨言,甚至还在设想她的未来——要读研、要成家...世间少有男人能做到如此地步,也少有人将爱屋及乌做得这般温柔。
你对姨妈的爱,是毫不遮掩的坦率,望向姨妈的眸子里总是漾着光,连声音语调都是不同于旁人的含情脉脉,因为你小心翼翼放在心尖上的人极重亲情,于是你便把我们也一同装进心里。
你,一向待我极好,每次我去乌市都是住在你家,你知道我无肉不欢,所以每次都会提前买好我最爱的烤全鸭,你知晓我爱读书,所以还专门赠我诗集;你煲的汤是世界上最好喝的,你的唠叨也是世界上最温柔的,你做的菜总是味道清淡,但每一次我都会极捧场地大呼好吃,而你每一次看见我夸张的动作总会嗔怪我咋咋呼呼,说我没有女儿家样子。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,你每次嗔怪后含笑的模样:弯弯的眉眼,微微上扬的唇角,还有浅浅的梨涡。现在,似乎只要我闭上眼睛,就能闻见菜香,还能听到那个隐隐带了笑却再也无法听到的声音说:“急什么,慢点吃。”
无论我如何逃避,都逃不了那个既定的事实。
人生在世,但凡肉体凡胎,千般遗憾,万般痛心都逃不了八个字:天灾人祸,溘然长逝。
2020年5月22日,是你离开人世的日子,也是我们从今往后都会铭记的日子。
听母亲说,当时姨妈在电话那头哭的撕心裂肺,母亲听到这个噩耗立刻愣住了,不能言语,正在值班的父亲匆匆赶来,扶起失声痛哭的母亲,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。姨妈飞去南疆,抱回了你的骨灰,而父母亲也匆匆赶往乌市,姐姐远在浙江本想赶回却被疫情硬生生困住,独自一人整日以泪洗面还要赶写论文。
所用人都在悲伤中奔波,日子仍在一天一天艰难地过,我似乎在成年人的世界里看到,即使再艰难也要走下去,可是我做不到,你的逝去对我来说是等同于失去一块骨头的剧痛,更是不敢触碰的伤口,而对于姨妈来说,你的离开意味着她毫无保留的爱情也随之消逝。
虽然时间仍在飞逝,但生活也确是发生诸多变化,变得混沌而慌乱,姨妈何等泼辣洒脱的人物,如今也变得缄默敏感,眼睛黯淡无光。你年迈的母亲和妹妹也受不了这令人痛心的刺激,整日以泪洗面,反复念叨,不过你不用担心,疼惜你的兄长和其他亲人都在妥善处理各项事宜,你的亲人们都很照顾姨妈,你可以放心。














 1392
1392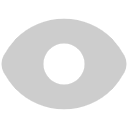 1674
1674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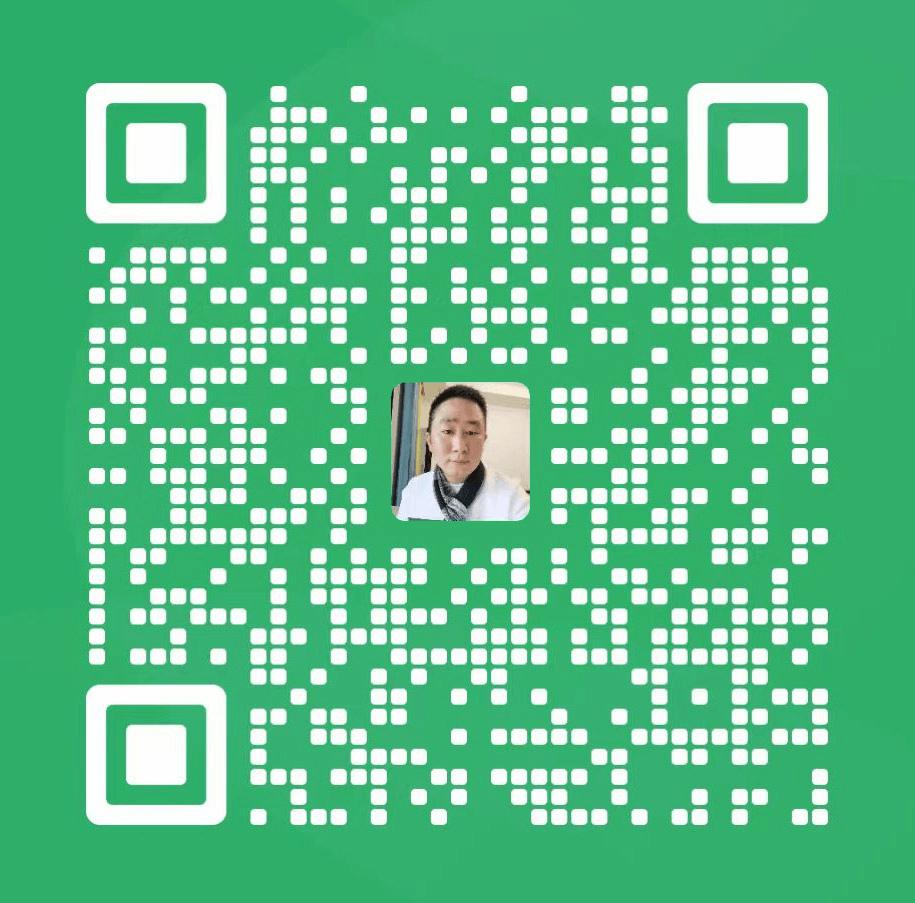




 创建纪念馆
创建纪念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