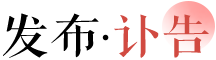悼词故事

连续写了四个月正经文章,不知读者因此正经了些没有,自己倒正经得有些招架不住,好像在与异性调情时说的是能上报眼的话,居家日常生活,却西装革履领带严肃一样,正经得过分,正经得不分场合地点,正经的让人感到你是巨心叵测。当正经得自感累的时候,自感没意思的时候,其实,离不正经已经很近了。在我看来,不正经,或有意的不正经,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坏事,有可能还是一种放松或自由呢,而令人可怕,或恶心的,是假正经。
现在,我们就不正经一回吧。
我要说的是,我长这么大,耍了这么多年笔杆子,目送过那么多人由人间走向天国,而我仅做过的两篇悼词。按说,悼词是再正经不过的文字,关乎着对一个消失的生命的怀恋,的悲伤,的追思,岂可不正经?按说,我做悼词的缘由很多,当过三年秘书,单位上很多重要行政公文都出自我手,这期间,本单位好几位同事死了,悼词却不是我写的。我不想写,因为那几句规定的干巴巴的词语给除了敌人的任何人都能用,既然给任何人都能用的话,写这种悼词有什么意思呢;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中,有好几位童年玩伴遇难而殇,有好几位少年同学死于非命,我也没有写过悼词,我知道,我的文字无法复原那一个个生动的形象,而我记忆中的他们仍是那么生动。他们死了,我悼念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活,而他们在我的心中本不死,笔下却死了,又怎能忍心使他们再死一次呢;还有我的几个老师,他们是名扬四海的学者,他们死了,各种悼念文章在各种媒体上纷纷亮相,悼念者一个个似乎悲痛得要追随而去,但我知道,在他们活着的时候,如今的这些涕泗交流的悼念者们,根本把他们没当回事,甚至盼他们早死,若果允许自由杀人的话,这一双双只可握住瘦笔杆的瘦胳臂们,早已向他们现今悼念的对象,不止一次地举起屠刀。人死了,他们眼前的山没了,他们便显得有些山的气象了,而借追述与倒下的山的源缘情分,就等于在给自个这座小山培土垫高罢了。我在这一篇篇悼词中看到的只是蝇营狗苟者的弹冠相庆。
也因此,我从不作悼词,尤其对我爱的人,我敬的人。然而,我还是做过两篇悼词的,这两篇悼词,至今还是朋友聚会时的笑料。
第一份作于1982年的冬天。我刚参加工作半年,每天早晨,我们这十几个刚分配到机关工作的小年轻,照例是要打扫办公室和院子的。那天,北风呼啸,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度。都是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,玩兴正大,并不把寒冷当回事。我们把废纸和树叶集中起来,在楼后的垃圾场焚烧。火借风势,风助火威,我们跳着,喊着,唱着,闹着,这时,一位学中文的伙伴摇头晃脑当场给我作了一篇悼词,抑扬顿挫,文采灿烂,大家乐不可支。我也大笑,笑完,我说,你们学中文的写文章容易堕入程式,我给你来一个别致的。我随口说道:
某某同志,生于1981年12月28日,卒于1982年12月28日,享年一周岁。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,是光辉的一生,他为国家节约粮食约二百吨,布匹约两千尺,其它物资不可胜计,他生如慧星之迅忽,死如闪电之耀亮。为了弘扬这种节约闹革命的精神,请大家向他致以崇高的革命的敬礼!呜呼哀哉,伏维尚飨。
举众为之绝倒。在那个寒冷的冬天,这篇悼词为我们刚踏上的人生之路制造出了一长串的欢乐。时光如贼,以特警之训练有素,也赶它不上,一眨眼,二十年的时光过去了,当年种种无状的毛头小子,不得不正经一些,哪怕是假正经,而在老朋友聚会上,当年在场的人都可完整地背诵我作的这篇悼词,引出幽远的温暖和如新的笑声。
第二篇悼词作于2003年9月26日。我随作家采风团去新疆周游一圈到喀什以后,采风团任务完成,要坐火车返回乌鲁木齐,可我想沿南疆和田一线,横穿塔里木和柴达木两大盆地,从青海回兰州。张弛先生,张存学先生也久蓄此意,三人一拍即合,便脱离大部队行动。漫漫流沙,迢迢驿路,各种辛苦与欢乐,片言难表。万里征程,无尽荒寒,我们终于到了青海的德令哈。张弛说,此处发现一个外星人基地,我们去看看。好不容易租到一辆曾去过那里的昌河面包,荒原上奔驰百里,到了目的地。这是一个叫玉素湖的所在,与身边的一个湖是姊妹湖,却一个是咸水,一个是淡水。玉素湖是咸水湖,外星人基地便在这里。司机带上情人躲到一块巨石后忙乎去了,举目茫茫,三人成众,水是虚假的清,天是虚假的蓝,云是虚假的白,不到此地,是决见不到那种概念意义上纯粹色彩的。三颗感恩的心被这万古荒原灼烧着。张驰兴起,要下湖游泳,不料,湖底青石板极为光滑,一跤跌倒,利刃般的石尖割破了脚趾,鲜血像一根红绸带,飘摇于光可鉴人的湖面。都吓坏了,一看,却无大碍。虚仅过后,他兴致更浓,倒给我俩作起悼词了。我俩不甘示弱,攻击他是张国涛,分裂了革命队伍,把我们引上了歧途。因为,他是作协副主席。
如果你对本文感兴趣的话,可以尝试点击下方按键“创建纪念馆”,为逝者进行祭奠。心纪奠是一款公益平台,支持云端祭扫、免费试用、永久保存。关注心纪奠公众号,点击立即建馆,随时缅怀和追忆。











 10432
10432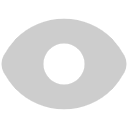 5764
5764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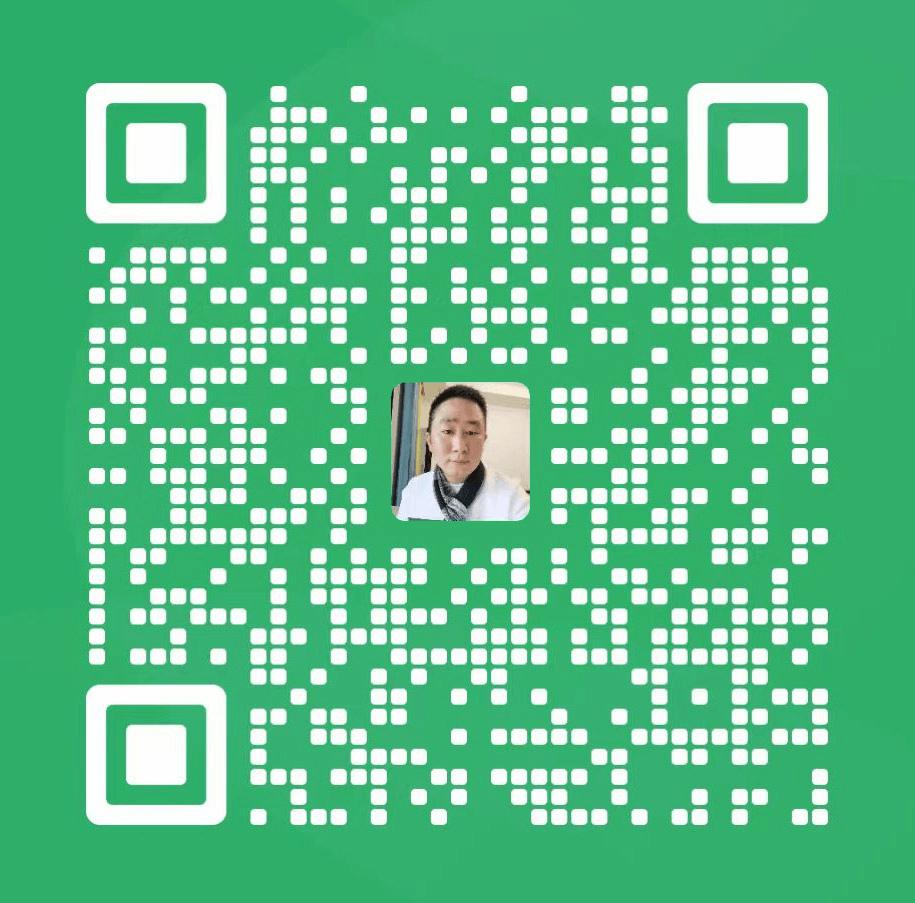




 创建纪念馆
创建纪念馆